讲座丨“新型革命”:反思尼赫鲁时期的印度
本文整理自2022年5月25日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讲座——“‘新型革命’:反思尼赫鲁时期的印度社会主义,1947-1964”(“ANewTypeofRevolution”:RethinkingSocialisminNehru'sIndia,1947-1964)。讲座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系副教授泰勒·谢尔曼(TaylorSherman)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谢侃侃助理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曹寅副教授和北大外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张忞煜助理教授参与讨论。泰勒·谢尔曼教授的研究领域为20世纪30-70年代南亚文化与政治史以及人民运动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动态关系,他近年来在ModernAsianStudies、SouthAsia:JournalofSouthAsianStudies、PostcolonialStudies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本次讲座基于她即将出版的专著《尼赫鲁的印度:七个迷思组成的历史》(Nehru'sIndia:AHistoryinSevenMyths)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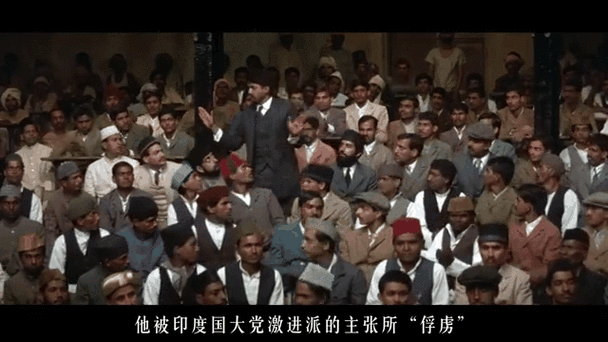
破除“印度社会主义迷思”1955年,印度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模式”为发展目标。然而,一些学者简单地认为,印度只不过在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印度的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变体;更糟糕的是,这种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并不适用于当时贫穷落后的印度。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印度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例如,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Bayly)便曾撰文指出,尼赫鲁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只不过是自由民主、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优生学等宏大学说的混合体。许多学者认为印度和苏联一样,都试图尽量借助国家的行政力量控制经济领域,致使私有制经济长期被压制。此外,他们还认为印度的社会主义更关注城市,却几乎忽略了农村地区。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Bayly)谢尔曼教授指出,这些都是“印度社会主义迷思”。实际上,在大多数印度社会主义者看来,印度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或欧洲的社会主义并不相同。因此,谢尔曼教授认为,想要破除上述印度社会主义迷思,就应该从印度社会主义的内部,用印度社会主义自身的表述来理解它。印度的社会主义者不应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群体。实际上,不同的印度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知都不尽相同。谢尔曼教授将印度的社会主义者大致分为三类,分别是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左翼(CongressLeft)、作为反对党的社会主义者(OppositionSocialists)(注:即独立后从国大党分裂出的、原国大社会党人及其追随者组建的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甘地社会主义者(GandhianSocialists)。虽然这三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但是大致的分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印度社会主义者内部的异质性。这三类印度社会主义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并在和苏联以及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对话中不断发展(注:与中国不同,在印度的政治语境中,社会主义者一般不包含共产党人)。印度的社会主义者们还共享了一套较为一致的观点,他们将其称之为“印度社会主义”。
印度社会主义的五个特点
印度社会主义具有以下五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印度的社会主义者都致力于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这在印度独立之初的二十年间体现得尤为明显。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是对英殖时期历史教训的反思。殖民政府将印度人视为一个集体进行管理,而对印度人的个体生活疏于关照。在反思殖民时期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关注个体的发展。其二是反殖民思想,尤其是圣雄甘地的反殖民思想。在谈到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时,甘地反对功利主义所倡导的“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格言,这意味着总有一些人会被抛弃,因此甘地提出了“共同繁荣、进步”(Sarvodaya)的原则。而印度社会主义者也秉持着类似的立场。
以《英印史》的作者、殖民史学家詹姆斯·密尔(左)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哲学主张用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社会效用,而圣雄甘地(右)则认为这一主张可能会漠视弱势群体第三,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1958年尼赫鲁指出尽管他“钦佩苏联的许多成就”,但他认为“只有给予个人发展机会,才能有真正的社会进步”。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将“个人”的内涵限定在白人、男性以及有产者,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印度社会主义者口中的“个人”,一般是指印度教上层种姓的男性地主。印度社会主义者便大多来自这一精英阶层。社会主义者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Narayan)认为,改造社会应当先从改造个人开始,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的自我革新。精英群体应该首先了解和改革自己的阶级,然后再将改革的热情转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
印度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关注劳动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劳动对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印度社会主义者看来,有目的的劳动还是自我表达和个人成长的方式之一。甘地社会主义者库马拉帕(J.C.Kumarappa)在书中写道:“为了成长,我们必须学习、劳动、玩耍、欢笑等。劳动对于培养高级能力的重要性就像食物之于身体一样。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应该有助于个性的成长。”这表明,劳动可以提升人民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成为新的、民主印度的合格公民。尽管印度的社会主义者都认同劳动的重要性,但对“劳动”概念的具体内涵却理解不一。国大党左翼和社会主义党人都认为,有目的的劳动首先指生产(making),而不是照护(caring)。他们往往更关注生产制造领域的劳动,并借此含蓄地贬低了大多数妇女所从事的日常家务劳动。不过,甘地主义者却认为,照护他人的劳动同样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的成长,但是,这项劳动要求照护者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和奉献。甘地主义者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将“赠予”作为促进社会和经济革命的一种手段。这一理念源于“献地运动”(BhoodanMovement)。(注:20世纪50年代初,甘地主义者维诺巴·巴韦(VinobaBhave)在海得拉巴发动了“献地运动”,呼吁地主将自己的多余土地赠予无地农民)随后,“奉献”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从最初的“献地”发展到“献力”(shramdan)、“献财”(sampattidan)等。而赠予的最高层次则是“献生”(jeevandan),即投身于改善印度农村生活的伟大事业,甚至为之献出一生。
维诺巴·巴韦(中间戴墨镜者)在印度农村开展“献地运动”印度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重视维护私有制。1948年1月,国大党经济委员会(TheCongressParty’sEconomicCommittee)报告建议逐步实现国有化。此举受到企业家们的强力反对,国大党政府被迫放弃了原定由国家接管大部分私营工业的计划。除了企业家们的抵制之外,印度社会主义者维护私有制也回应了农民的呼声。后者强烈要求拥有自己的土地,因此,许多社会主义者都呼吁重新分配私有产权,而不是废除私有制。社会主义者们并不强调集体化或国有化,而是希望通过合作社来促进民众协同合作。然而,这种振兴乡村社区的乌托邦式愿景并非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合作社“本质上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中,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有“道义上的责任来帮助经济上弱势和社会地位落后的人”。也就是说,这种互助形式的制度基础依然是种姓和阶级。没有人试图正视这些等级制度的起源,也没有人尝试减轻几个世纪以来强加在低种姓和落后阶级身上的痛苦。
由此可以引申出印度社会主义的第四个特点:不追求绝对的平等。独立初期的印度经济落后,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民族主义者斥责英国耗尽了印度的财富,并向人民承诺改变这种局面。然而,社会主义者却认为不可能彻底消灭地主、资本家和官僚阶级,应该以更为仁慈的态度对待他们。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不是实现阶级平等,而在于尽量减少极端的不平等现象。尼赫鲁的内阁成员、印度第一任卫生部长阿姆里特·考尔(AmritKaur)认为,“绝对的平等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多样性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将认识到多样性可以惠及他人。”
印度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对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缩影,其主要目标是使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然而,如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五年计划的设计者们其实另有考量。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设计师马哈拉诺比斯(P.C.Mahalanobis)将经济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大型工业部门,他认为在这一领域国家指令应该居于主导地位。另一个领域是国家难以发挥作用的“弥散”(diffuse)部门。一项调查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弥散型或非正式组织部门为印度提供了90%的就业岗位和84%的国民生产总值。从中可以看出,即便是国大党左翼,同样认为国家在大多数经济领域的干预实际上非常有限。
印度社会主义在城乡的具体实践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度工业领域的国有化程度相当有限,仅包括航空业、人寿保险业、巴士运输业以及电力行业的一部分等少数几个领域。也就是说,国有化实际上只是印度社会主义计划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大党在工业领域的核心举措。当时,尼赫鲁呼吁企业家与政府携手合作,造福人民。根据印度劳动和就业部的数据,截止到1961年,中央政府共制定了30部法律,各邦政府也制定了82部法律以保障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和福利待遇。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保护工人的权益,但是仍有很多公司违反法律、偷税漏税、侵害员工利益。不过,也有部分行业和公司积极落实了政府的要求,自行车企业森-罗利(Sen-Raleigh)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印度在独立之后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对进口工业制成品征收高额关税,同时扶持民族工业发展。孟加拉人苏提尔·库马尔·森(SudhirKumarSen)响应这一号召,与英国自行车生产商罗利(RaleighCycles)组建起合资公司森-罗利,并于1951年在西孟加拉邦的坎雅普尔(Kanyapur)建立了第一家工厂。可以说,森-罗利公司符合许多社会主义者对印度私营企业的设想:它既是民族工业,但又没有被国有化。工厂吸引了周边地区的许多民众前来工作,而森-罗利公司也履行了相应的社会义务——公司尽力为员工营造良好的居住条件,在工人的聚居地建设住房、栽种植被、配置电力设施、卫生设施和儿童游乐设施等。尽管森-罗利公司并非国有企业,但政府也提供了各类直接支持,如发放许可证、培训工人、把关原材料等。可以看出,印度社会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私营部门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带来的协同效益。社会主义政府可以为私营工业提供各种支持,如进出口管制、资金支持、技术培训、平息罢工等;而企业则需要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并缴纳越来越多的税款。
左侧为森-罗利公司的自行车广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拥有自行车是印度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对印度社会主义的另一个迷思是印度效仿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忽视农村地区。直到绿色革命之后,农民的境况才有所改善,印度才开始实现粮食自给。谢尔曼教授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她指出,在印度独立之后,要求土地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印度共产党在海得拉巴的特伦甘纳地区领导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要求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就在这时,甘地主义者维诺巴·巴韦(VinobaBhave)发动了“献地运动”,希望改善特兰加纳地区农民的物质和精神境况,以与共产主义运动对抗。当时,他在特伦甘纳地区走访,了解农民的具体情况,“传播关于爱、信任与和平的信息”。在一次集会上,几个达利特家庭乞求他想办法给他们土地。巴韦开始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但随后他突然想到,可以请在场的人把土地捐献给无地者。一位地主当即同意捐出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巴韦由此受到启发,并决定把这一“牺牲”行为转变为一场人民运动。他四处演说,呼吁人们捐出自己的多余的土地。尼赫鲁写信给海得拉巴政府,要求他们尽可能地为“献地运动”提供支持。邦政府迅速采取行动,立法支持这一运动。
尼赫鲁与“献地运动”的发起者维诺巴·巴韦总的来说,印度的社会主义确实存在计划经济成分,主张国家干预调控部分关键性行业。但是,这仅仅是印度社会主义的一小部分。并且,这种做法并没有背离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反,这就是印度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
评议与讨论
在评议与讨论环节,曹寅老师指出以往的研究常将尼赫鲁与现代化、世俗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而谢尔曼教授的研究修正了学界对尼赫鲁的刻板认知,提醒我们不应过分高估国家在印度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的作用。曹寅提到,1945年8月14日尼赫鲁发表独立演讲时多次强调了一个“新印度”(NewIndia)的诞生。这里的“新印度”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印度”,而与之相对的“旧印度”则是殖民地印度。有趣的是,拉文德·考尔(RavinderKaur)在他的书中谈及21世纪的印度时,也使用了“新印度”一词。此时与之相对的“旧印度”则可能是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印度。当前,印人党政府正在尝试解构尼赫鲁,这启发我们思考“新印度”等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
张忞煜老师认为,中国学界对印度独立后史书写也和英语世界一样,深受印度民族主义史学影响,较为关注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强调国家如何借助计划经济,推进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印度的意识形态多样性,因此本讲座提出的“从印度社会主义自身的表述来理解它”的观点极具启发性。另外从讲座中也可以得知,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力量都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是由许多人建构出来的,这启发我们思考应该如何界定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此外,他还关注共产党人等左翼力量如何看待尼赫鲁以及国大党政府的社会主义实践。印度共产党人可能并不认同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在一部分激进的共产党人眼中,尼赫鲁政府腐败横行,背叛了民族主义运动时期的承诺,令人失望。
从事东南亚研究的谢侃侃老师则将尼赫鲁与同一时期印尼的领导人苏加诺进行对比。他认为,这两位领导人都和社会主义关系紧密,但是他们实践社会主义的方式却颇为不同。作为一个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试图平衡各种政治力量,由此提出了纳沙贡(Nasakom)的政治理念,主张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的团结协作。苏加诺常常联合印尼共产党推进一些较为激进的政治议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政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在苏加诺的统治时期,印尼国内的政治局势迅速激进化。相比之下,尼赫鲁及其他印度社会主义者更主张通过非暴力等较为温和的方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谢老师对两国社会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表示关注。
苏加诺与尼赫鲁(图为1950年1月26日苏加诺作为外国领导人出席印度首个共和日时的合影)
谢尔曼教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关于“新印度”的问题,她认为,后殖民时代的国家总是在不断地重塑自身。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印人党就开始指责尼赫鲁和国大党政府未能兑现其改变印度的承诺。印人党认为,尽管尼赫鲁和国大党承诺建立一个新的印度,但是直到今天,印度仍然充斥着腐败乱象,发展停滞不前,和殖民时代并无太多不同。印人党在批判国大党执政历史的同时,致力于构建一个不同于国大党的“新印度”。
关于如何界定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谢尔曼教授认为,它更多是一种试验主义。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印度的宪法还是在尼赫鲁的书中,都没有一套关于社会主义的固定看法。社会主义者们实际上会在各类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修正自己的观点。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国际化。以往我们可能会认为印度主张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因此在国际上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但事实上,印度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许多印度精英在进行社会建设时都尽可能地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
关于共产党人等左翼力量对尼赫鲁以及国大党政府的态度,谢尔曼教授指出,共产党人确实有他们自己的立场。他们批判政府,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比执政党更好地管理印度。但是实际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尼赫鲁并无太多不同。例如,1957年第二次大选前夕的民意调查显示,尼赫鲁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而且他在左翼力量中的支持率也非常高。这是因为左翼力量认为,如果一旦尼赫鲁下台,则很可能由更加右翼的领导人接任总理,因此他们宁愿选择支持尼赫鲁。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尼赫鲁的温和社会主义相对满意。另一个例子是印度共产党1957年-1959年在喀拉拉邦的执政经历。印度共产党在这一期间延续了先前国大党的执政措施。他们承诺不会进行国有化,主张遵循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模式。这表明,左翼力量和尼赫鲁的国大党在国有化、国家干预等方面存在共识。
关于尼赫鲁和苏加诺在实践社会主义时采取的不同方式,谢尔曼教授从尼赫鲁的角度进行分析。她猜想这可能是和尼赫鲁的性格以及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尼赫鲁更像是一个高种姓的、接受过外国精英教育的贵族。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尤其是印巴分治的1946-1948年间,印度经历了大规模的暴力活动,这些暴力活动在短时间内就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亡,印巴分治带来的惨痛经验促使尼赫鲁格外警惕暴力行为带来的巨大伤害。此外,非暴力的理念也是甘地留下的政治遗产。可以看到,甘地一旦发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超出了控制——例如1922年乔里—乔拉事件(注:1922年,印度联合省乔里—乔拉地区的民众在参与不合作运动的过程中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伤亡,随后甘地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他就会下令停止运动。尼赫鲁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甘地的非暴力理念。加之印巴分治带来的创伤,更使他倾向于通过温和的非暴力的方式推行自己的政治议程。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